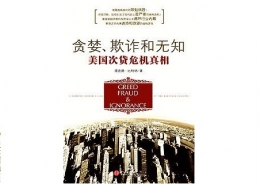老年喪偶是人生莫大的打擊。我看到了72歲的媽媽在父親過世後這兩年多來,如何努力再度活出生命的光彩。
英國詩人威廉.華茲華斯(William Wordsworth)在〈我們是七人〉(We are Seven)長詩中寫著:「一個單純的孩子,過他快樂的時光,興匆匆的、活潑潑的,何嘗識別生存與死亡?」就像孩提時朗誦杜詩,哪裡識得人間苦?直到叔叔壯年辭世,當殯葬儀式結束,眾人散去,為鄰十年的叔叔就這樣被我們留在荒煙蔓草中,我才驚覺此刻牽著我的爸爸也不會是永久的存在。年紀漸長才稍稍讀懂詩,讀懂《詩經.唐風.葛生》中的死生契闊。
父親猝逝,衝擊最大的是與他相依為命的母親。父親的好脾氣與愛妻愛家在村子裡是出了名的。他一走,在生活大小事上完全倚賴父親的母親,徹底慌了手腳。鄉下秀美的風景,徒增景物依舊、人事已非的感傷;沒有子女在側的獨居生活,乏味至極。她數度表示人生走到這一步,真的很沒意思。
還記得父親去世後約三個月,我以陪我騎腳踏車為名,說好說歹、半強迫地要媽媽出門透透氣。我騎在媽媽的後頭,看著她微胖的身軀,想起她還是年輕小姐時的美麗照片,想到媽媽也曾經是天真無憂的小女孩......一個生命一生中,除了生老病死的必然,還要經過多少挫折磨難?我雖為么女,但在媽媽面前,一向表現堅強。在這段靜默的路上,我卻無法忍住在媽媽背後數度掉淚,深感當一個「人」本質上無法迴避的孤楚。
所幸鄉下人情味濃郁,這兩年來,親戚鄰居不時探望陪伴,母親也報名了日文課,並到附近的學校當愛心媽媽,日子終於漸漸上了軌道,吃東西不再食不知味,艱難的程度好像是雙腳殘障的人士重新學習站立一樣。
今年夏天我回老家陪媽媽住一段時間,每天傍晚我們都會到屋後的小路散步、吹吹風。剛走了十分鐘,媽媽突然指著路旁右側說:「妳看,怎麼這麼漂亮!」我湊過去看了半天,並沒看到特別豔麗的花朵。媽媽見我找不著,用手指著前面貌似鬼針草的植物,讚美它的球狀弧度那麼完美!
我依然在母親身邊跳躍前進,手舞足蹈地擁抱粉彩的天空與沁涼的微風。一回頭,忽然看見母親在小路左側又停了下來,在那兒專注地側耳傾聽。我好奇地走到媽媽身邊,她說:「妳趕快來聽,這裡有兩隻青蛙在對唱!」見她右手一指,右邊草叢果然響起一聲音調特低的蟲鳴;她接著舉起左手引導我注意左邊被枝葉覆蓋的溝渠,不一會兒,還真的從裡頭發出一聲相應和的「男低音」。媽媽繼續信心滿滿地指右指左,那兩隻青蛙竟也給足了面子乖乖地一唱一和,沒讓媽媽「漏氣」。此時的母親像極了一位神氣的田園交響曲指揮家!
走著走著,媽媽又發現了草叢中有一個體積是兩個籃球加起來的大南瓜,遠處還零星散布著幾個,我很訝異農業改良場也培育這種品種。媽媽說她之前刨絲、曬乾自家種的南瓜,加入其他中藥材磨成粉給大哥吃,大哥說吃了以後身體感覺不錯。媽媽自語著回去以後還要再多做一些才好。
大哥隨口的一句話,就能讓媽媽忙上好幾天,心甘情願。為人父母果真是天下最傻的傻瓜。大哥都年近半百了,在兩岸三地闖蕩多年,可在母親心中,他永遠只是她親愛的孩子。也許也是因著對子女的牽掛,才讓媽媽勇敢地走到今天吧。
散步完回到家,晚餐時我問媽媽:
「剛剛飛在那一大片休耕地上的大白鳥是白鷺鷥吧?」
「對啊。」
「種咖啡樹的那塊地,水溝旁邊長的是什麼花?」
「嗯......」
我見她好像想不起來,補充說明:
「粉紅色,花瓣上有直條細紋。是不是水仙?」
「不是。」
「蘭花嗎?」
「不是。」媽媽搖搖頭:「怎麼一下想不起來?」她低頭繼續喝著玉米湯。過了一會兒,媽媽抬起頭,眼睛發亮地說:
「是孤挺花!」
「媽,妳確定嗎?」
「對啊。」
「妳真的很確定喔?」
「嗯?妳是不是要寫文章?」
我笑而不答。
媽媽忽然揮舞起右手的筷子,上下比劃著說:「寫文章的人是不是眼睛看出去,世界就像一首詩?」
我不禁噗哧笑了出來!這句話本身不就充滿著詩意嗎?家居散步,是我最鍾愛的時刻。在夕陽的輝光中、在母親與我的相互陪伴裡,我由衷地感激這平凡中上天的祝福。